首頁>收藏·鑒寶>資訊資訊
6000張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圖像 在線免費觀看
上個世紀80年代,法國收藏家皮埃爾·德·吉戈爾(Pierre de Gigord)曾在土耳其收集了數千張奧斯曼帝國時代的攝影圖像,并由此成立了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它如今坐落在蓋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內。蓋蒂研究所最近對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6000多張照片進行了數字化處理,使其可供免費在線學習和下載。

吉戈爾的這套圖片合集包括各種介質和格式,從蛋白印花到幻燈片,從玻璃底片到相冊,豐富多樣。它們記錄了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余暉,從地標建筑到城市風景,從自然景觀到考古遺址,經過數字化后,奧斯曼帝國居民100多年前的繁華生活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伊斯坦布爾的艾敏厄努廣場(Emin?nü)集市和耶尼清真寺(Yeni Cami, 新清真寺),商店標志上有奧斯曼土耳其語、亞美尼亞語、希臘語和法語,1884-1900,Sébah&Joaillier攝。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在扶手椅上游歷奧斯曼帝國時代
因為媒體介質的多樣,圖片庫中既有長幅全景圖,又有口袋大小的名片,這給圖像的數字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挑戰。比如君士坦丁堡的10組全景圖,需要將各自獨立的蛋白印花拼接在一起,才能創造出1878年伊斯坦布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壯觀的天際線全景。現在經過數字化處理后,它可以在屏幕上完整地被觀看。又比如維也納商業區Josef Sengsbratl的50張手工彩色幻燈片,需要校準正面和背光,以捕捉彩色圖像的暖色調,呈現商業信用名稱和地址。
圖像經過數字化后,人們既可以在教育場所放映這些圖片,也可以在私人住宅里的屏幕上作為消遣觀看,如此一來,觀眾就成了“神游旅行者”(armchair traveler)。通過這些圖像,人們可以了解過去土耳其的男人和女人、工藝品和商業貿易、奧斯曼帝國首都的標志性建筑、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以及該地區的地緣政治。

搬運工搬運繩索,Josef Sengsbratl攝。手工彩色玻璃燈籠幻燈片。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在吉戈爾的圖片庫中,82個玻璃板底片被數字化并變成正片,人們因此可以隨時訪問這些圖像,其中包括這張熙熙攘攘的街道圖片,它展現了世紀之交處于歐洲一側的奧斯曼首都景象。

繁忙的街道,君士坦丁堡,1890年,攝影師不詳。玻璃板底片。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圖像的第一人稱視角
還有60多部攝影相冊進行了數字化處理,我們因此有機會閱讀那些曾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旅行的收藏家和攝影師們獨特的私人記敘。在相冊“土耳其=小亞細亞1917-1918”(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中有一張照片:一位德國軍官將他的照片獻給了一個遙遠的“心愛的寶琳”(beloved Pauline)。這份相冊文件證明了亞美尼亞大屠殺期間德國軍隊在土耳其的存在,這與那位軍官的浪漫奉獻形成鮮明對比。
根據標準的數字化實踐,該相冊不僅會逐頁拍攝,而且還會逐張詳細拍攝,以便讀者更真切地體驗圖像的細節特寫。網站上注解圖像所用的整潔字體和精心排版的照片進一步表明了工作者的嚴謹態度。下面的四張照片是“土耳其=小亞細亞1917-1918”中的一頁,呈現了土耳其的城市、市場、被毀掉的某處場所以及戰爭部長恩維爾·帕夏
(Enver Pasha),他是亞美尼亞種族屠殺最大的肇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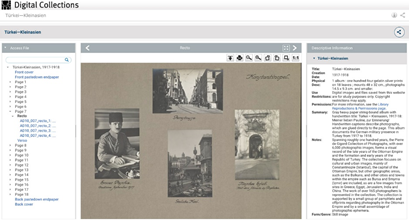
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第7頁。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相冊還包括街景和日常生活的圖像,比如街頭小販和居民,下面這頁圖冊展現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女人,她正對著攝影師微笑。

Türkei= Kleinasien 1917-1918,第16頁。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被湮沒的過去
許多學者已經將吉戈爾的圖片庫運用到自己的學科研究中,從土耳其建筑、考古學到古物研究,從拜占庭和伊斯蘭藝術到后殖民研究、攝影史,領域多種多樣。
藝術家Hande Sever最近在The Iris上強調了亞美尼亞攝影師在塑造土耳其民族文化歷史和集體記憶方面發揮的核心作用。吉戈爾的數字化圖像對這個百年前繁華帝國世界的人物、建筑、城市空間與風景的記錄,與已故亞美尼亞攝影師阿拉·古勒(Ara Güler)的作品形成了某種對照,很值得引起注意。古勒的照片和家族歷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果的展現,他在亞美尼亞大屠殺時失去了祖父母,后來為攝影機構Magnum工作,并建立了一個包含90萬張照片的檔案庫。

一艘渡輪停靠在伊斯坦布爾Salacak鄰近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岸,1968, Ara Güler攝。圖片來源:Magnum Photos。
值得一提的還有另外一個人,2006年獲得諾獎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他曾使用古勒檔案庫中的圖片來為自己的小說做注解,那些作品都是以20世紀的伊斯坦布爾為背景。為此他還曾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中向古勒致敬。帕慕克寫道:通過攝影師的照片來看19世紀的土耳其,不僅美麗,而且重要,因為在視覺記錄和個人記憶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一條街道也許會使我們想起被解雇的痛苦;一座橋也許會將我們帶回到青春歲月的孤寂中;一片城市廣場也許會使我們回想起一段快樂無比的愛情;一條黑暗的小巷也許會使我們突然充滿政治的恐懼;一個古舊的咖啡館也許會使我們想起那些被監禁的朋友;而一株美國梧桐也許會讓我們想起過去的我們是多么貧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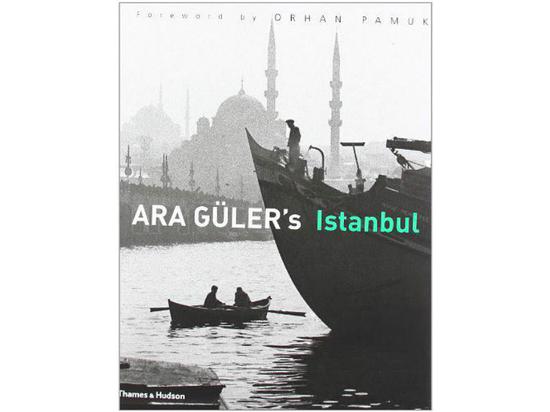
作者:阿拉·古勒 奧爾罕·帕慕克
版本:Thames and Hudson Ltd,2009年
Hande Sever和帕慕克直接或間接地評論了亞美尼亞攝影師在塑造土耳其民族和文化認同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視覺記錄作為一種逝去世界記憶的獨特價值。奧斯曼土耳其就是這樣一個逝去的世界,因為時間和現代化的蹂躪,因為戰爭,因為民族主義和種族清洗而徹底消失在歷史中。
19世紀圖像的數字化,使我們能夠了解過去,了解土耳其的多元化社會、傳統、習俗和城市構造。同時也使我們了解現在,了解一些社會問題是如何持續發展卻仍然受過去所縛。

加拉塔大橋(Galata Bridge),約1875-1889,Guillaume Berggren攝。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物質靈暈的消逝
在數字環境中,這些圖像將從其原始的物理環境中刪除。只是沒有物理存在的支持,比如格式或尺寸,我們可能無法把握圖像的某些物質特征。不過對原始圖像訪問機會的增加使我們能夠想象和體驗過去,并勾連起過去與當下的聯系。
比如這樣一個場景:一個男人在給兩個女孩讀信,兩個女孩安安靜靜、全神貫注地聽著。這個場景中所包孕的寧靜與親密的感覺甚至超越了時間。我們可以想象,這張照片是如何時時在它的擁有者那里喚起不可磨滅的記憶的,它的主人或許將它珍藏在抽屜里,或許懸掛在墻上,或許保存在私人家庭相冊中。

男人為兩個女孩讀信,1890年,攝影師不詳。來自Pierre de Gigord Collection中的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共和國圖片集。蓋蒂研究所。
康奈爾大學的元數據圖書管理員Jasmine E。 Burns在她的文章《物質性的光環:數字代孕和攝影檔案的保存》(The Aura of Materiality: Digital Surrogac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hotographic Archives)中解釋了將照片進行數字化歸檔的過程,就像從負片中打印正片一樣,使圖像適用于更廣泛的用戶。通過和原始來源的分離處理,圖像本身因為在不同環境中同時存在而展現出新的意義和解釋。
復制圖像的物質靈暈在數字化的過程中可能會丟失,但吉戈爾的照片所記錄的居民生活,他們的手勢、姿勢、表情、情感和行動,都可以被重新闡釋,因為他們的歷史可以被更多的人所看到。下圖展示了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Trabzon)的五張照片。底部三個城市的視圖提供了高對比度的敘事背景:在上面一排圖片中,兩個庫爾德匪徒
(Kurdish bandits)由超過被行刑者的20多名憲兵處決,與之并置的是一對沖著鏡頭擺出優雅姿態的夫婦。這組照片呈現出一種生與死的強烈現實分歧。

從左上方順時針方向:庫爾德匪徒被土耳其憲兵捕獲并執行死刑、黑海沿岸城市特拉布宗、一對來自特拉布宗的夫婦、港口和有軌電車,1885-1995,攝影師不詳。蓋蒂研究所。
(此文編譯自蓋蒂研究所Isotta Poggi的 “Ottoman-Era Photographs Take on New Meaning in Their Digital Life”,原文發表于The Iris,文章有刪減改動。)
編輯:楊嵐
關鍵詞:圖像 奧斯曼 土耳其 圖片




 走進塔吉克斯坦納烏魯茲宮
走進塔吉克斯坦納烏魯茲宮 也門霍亂病例激增
也門霍亂病例激增 2019亞洲商務航空大會及展覽會開幕
2019亞洲商務航空大會及展覽會開幕 世界園林巡禮——日本大宮盆栽美術館
世界園林巡禮——日本大宮盆栽美術館 巴黎圣母院:浩劫之后
巴黎圣母院:浩劫之后 鄱陽湖畔的瓜田“跑道”
鄱陽湖畔的瓜田“跑道” 唐山港一季度吞吐量超1.6億噸
唐山港一季度吞吐量超1.6億噸 第十一屆“勇士競賽”國際特種兵比武在約旦拉開戰幕
第十一屆“勇士競賽”國際特種兵比武在約旦拉開戰幕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