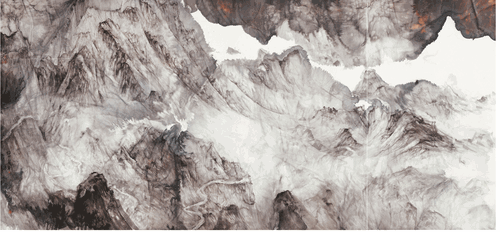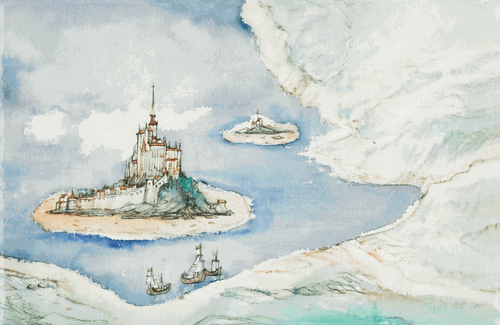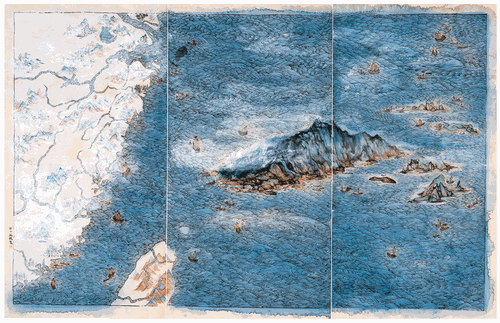首頁>書畫>畫界雜志>2023年第三期
樓外峰千朵——丘挺的“傳統”與“現代”
丘挺在“傳統”方面是驕傲的。確實,他有資本如此。早在本科畢業時,他臨摹的《青卞隱居圖》便以驚艷的方式,展現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傳統底蘊。于是,年少得名的丘挺在諸多前輩關注下由南而北,并迅速在北京成為名家。彼時,基于扎實的筆墨功夫與寫生的靈動,他備受學界關注,博士畢業后便“高調”落戶中央美院國畫系。此后數年,丘挺潛游于“傳統”,不僅筆耕不輟,且勤于鑒藏。宋元明清之諸多名跡,或過眼之緣,或置之案頭,賞玩之余更是目識心記,骎骎然而為同儕所羨。因此,“傳統”之于丘挺,非日誦其一的學習課程,而是接踵摩肩的生活記憶。其實,“傳統”的學習就應如此“浸泡”。很多人高舉“傳統”卻未得其真的原因,正是將傳統僵化為一二三的“特征口訣”,故而難能深入其中溫火煨燉。丘挺很幸運,從年幼學畫到少年求學,一直受到頗為正宗的傳統教育,并形成自己有關傳統的理解方式。
山外之山中之一(國畫)263×550cm-2020年-丘-挺
如2008年的《武當山系列》,丘挺選擇紙面較為粗糙的皮麻性宣紙,以皴擦帶墨,形成如煙如玉的筆墨氤氳,復以稍重的健挺之筆勾壓畫面,寫生狀物的同時兼顧了筆墨的節奏與律動。其實,這一特點正是新時期以來傳統筆墨與寫生結合的突出成果。如果將目光投諸20世紀山水畫整體發展中,我們會發現:實景寫生的畫面空間感在20年代進入中國后,并未與傳統文人畫之筆墨經驗充分“融和”,而直接跳轉50年代的語言創新—李可染式積墨光影以及傅抱石式“抱石皴”之類的“寫生”。應該說,在新時期“傳統再認知”的潮流中,陸儼少等人影響下的中國美院的一批青年畫家,填補了這一“空白”—中西碰撞過程中的“邏輯缺失”。他們以筆精墨妙的“寫生”,完成了西畫空間體驗與本土語言的完美結合。毫無疑問,丘挺是這批畫家中的佼佼者。
太行幽谷圖(國畫)450×35cm-2015年-丘-挺
但是,與1990年代開始出現的“筆墨寫生”中的絕大多數畫家不同,丘挺并不滿足于此。他工作室的醒目位置掛了一張六田知弘拍攝的《那智瀧》,暗示了他糾纏于“傳統”時的“不安分”。毫無疑問,這是一張具備現代主義特征的攝影作品,日本和歌山縣那智瀑布在這件作品中被表現為黑白分明的形式構成。雖然,我們仍然能在六田知弘的“黑”與“白”中,找到類似中國水墨的質地—高級的透明與純凈,但它極具視覺開合的沖擊力,卻與中國山水畫迥然不同。很難想象,糾纏于“傳統”的丘挺,在自己工作的空間中,沒有掛一張二玄社印制的“古畫”,卻選擇了一件這樣的攝影作品。亦因于此,被裝裱為立軸的攝影作品,成為一種隱喻:深諳傳統之道的丘挺對“現代”的開放態度。
圣米歇爾1(國畫)20×30cm-2014年-丘-挺
這是感知系統的開放:不將“傳統”視作沉重的古訓,而試圖將它們轉變為今日語境下的視覺資源。應該說,這種開放性不僅體現為丘挺在工作室中懸掛的“裝飾品”,也表現在他的創作轉向中。大約2014年前后的作品中,丘挺的“筆精墨妙”發生了一些細微變化。如《理坑寫生》,雖然一如此前江南小景寫生,但筆頭的手腕動作減少了,轉而更加注重墨的自然水韻。于是,畫面的線性因素減弱,輕盈潤透的塊面因素增強。這種“變化”看似偶然,但將之置于前后的作品序列中,我們卻隱約察覺到某種主動性的選擇。又如2015年金箋水墨《太行幽谷圖》系列,“傳統”山水的圖式只是水墨構成的基礎,物象表達退居二線,成為畫面的某種暗示性。有趣的是,這一年恰是丘挺委托朋友從日本購得六田知弘攝影作品的時間。
2015年,在丘挺的作品序列中值得重視。這一年,他不僅購得六田知弘的《那智瀧》,自己也創作了兩張名為《華嚴瀧》的作品:一張橫向淡墨;一張縱向重墨。將兩張《華嚴瀧》放在一起,我們發現傳統與現代的視覺感知方式,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融和”。橫向淡墨的《華嚴瀧》,仍以傳統筆墨趣味為主,但瀑布與云氣的交叉留白,卻分明帶有現代構成感;縱向重墨的《華嚴瀧》,視覺上類似六田知弘攝影作品,強調黑白沖突的開合構成,但細節處的積墨與皴擦,卻仍然具有一種傳統筆墨的質地。從某種角度看,這兩件創作于同一年的《華嚴瀧》,委婉地向觀者傳達了畫家彼時的思考—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萬壑幻雪(國畫)128×68cm-2020年-丘-挺
傳統與現代,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是一對無法回避的概念。它們往往與中西、古今混合在一起,成為文化抉擇中難以清晰化的“矛盾”。之所以成為“矛盾”,則是因為大多數人面對這些概念時,采用了二元對立的思考前提,即傳統與現代不可兼容。于是,持現代視角的人,認為傳統就是守舊,并冷眼相看;持傳統視角的人,則認為現代就是模仿,亦嗤之以鼻。殊不知,如此種種,皆為一葉障目,難能真正面對20世紀以來中國融入世界的現實語境—傳統與現代互為生長的歷史事實。有鑒于此,出身傳統“名門正派”的丘挺,試圖在認知層面上,消解這種“二元對立”,以期獲得更為自由的視覺感知力。就此而言,他與“華嚴瀧”的機緣,似正是這種認知觀念的“必然”結果。無論橫向還是縱向的《華嚴瀧》,他對墨法的重視程度,越來越超過對筆法的看重。這在他后來一批金箋作品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如2017年所作《山外之山中》系列,丘挺利用金箋的物質特性,以筆帶墨形成濃淡塊面的視覺構成感;2018年創作的《小雪》,構成感的濃淡對比,恰如六田知弘的“攝影”。金箋之外,紙本作品如2016年的《布魯克納第四交響曲》,亦然。這件以音樂為名的五聯畫,除少數點景樹木,完全就是情緒化的“視覺構成”假借于水墨而流動。
華嚴瀧(國畫)36.1×46.5cm-2015年-丘-挺
基于如此邏輯,丘挺后來的創作中出現《終南山上》這樣的作品,就不再令人奇怪。這件2021年創作的絹本山水,在他的作品序列中看似突兀,卻是2015年后創作邏輯的自然生發。熟悉中國繪畫史的讀者,很容易在這件作品中找到《晴巒蕭寺圖》的建筑物,但卻找不到那種熟悉的宋畫風格。顯然,精心“再造”晴巒蕭寺的丘挺,并不想臨摹一張古畫。他用自己對建筑與山川的理解,為古畫中的建筑物重構了“山水情境”。值得注意的是,丘挺用以重構情境的語言,正是帶有現代主義形式構成的“山川”。將《終南山上》的構成性對比他此前的金箋作品,兩者間的脈絡關系自然顯現。于是,《終南山上》宛如圖像的隱喻:經典圖式與現代圖式,具有某種對話契機。當然,丘挺對這種“對話”并沒有設置最終答案。顯然,他更享受“過程”的開放性。因此,丘挺無意間打開了一扇通往圖像觀念的大門:通過“文本再造”重建圖像的意義。晴巒蕭寺中的“古剎”,在原作中是一種意象符號,指向深山幽居,指向古意與修行,具有文學化的修辭屬性。但在丘挺的筆下,這種文本意義不復存在。可以想象,不具備中國古典山水畫閱讀經驗的人,面對《終南山上》的塊面與構成,很難感知出山川空間。此時,點綴于其間的“古剎”便成為一種“空間想象”的引導者,使那些看似抽象的畫面形式,成為一種空間性的存在物。基于此,建筑物在古畫中所具有的文學化的修辭意義消失,轉而成為空間性質的圖像本身。
讓文學性質的畫面回歸圖像本身,這與現代主義興起之初的“反文學性”,看似具有了某種藝術史邏輯的關聯性。這或許并非丘挺的創作本意。但他的作品能夠出現如此的闡釋空間,卻正是得益于他對“傳統”所持有的開放性。毫無疑問,丘挺是一個敏感的畫家,不僅對視覺語言敏感,也對視覺背后的觀念保持了自己的敏感度。因此,他在創作中時常出現一些溢出傳統中國畫邊界的“嘗試”。如2014年創作的《圣米歇爾》絹本系列,這組作品以法國天主教圣地的圣米歇爾山為對象,看似寫生實則重構了教堂城堡的“真實性”,使之成為精神象征符號的“實景”。尤其《圣米歇爾1》,以傳統中國山水畫的鳥瞰視角將圣米歇爾山置于整個海灣之中,制造了一種奇幻的視覺空間。這幅作品中,作為知識經驗的輿圖與作為審美經驗的山水,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視覺互動”。應該說,這種圖像經驗處于藝術與非藝術的縫隙中,并因此產生針對傳統審美性繪畫的檢討價值。
釣魚島(國畫)190×295cm-2022年-丘-挺
有趣的是,《圣米歇爾1》的創作偶發性,在丘挺的作品中并非孤例。如其2021年所作《寫生路線圖》,便將這一特征更為顯著地放大了。從某種角度看,這種嘗試已經遠超傳統山水畫范疇。他用如煙如玉的墨色構成,象征性地描繪了一幅世界地圖,并意象性“標注”出他的寫生地點。之所以將“標注”一詞加上引號,是因為它并非地圖性質的“符號”,而是美學性質的“山水”。顯然,這件作品中的尺度關系是“失常”的,無論目標地與整個空間的關系,還是地圖內的區域關系,丘挺都沒有以科學的知識經驗面對,而只是借用地圖在視覺表達上的形式特征,展開知識性的理解方式與山水畫的美學經驗之間的“對話”,亦如《終南山上》中,經典圖式與現代圖式的“對話”。
在“對話”中尋找傳統的開放邊界,似乎成為丘挺在創作中時常發生的現象。這使他和很多傳統出身的畫家不同:在驕傲于傳統的同時,包容現代。誠如,丘挺癡迷蘇州拙政園的“與誰同坐軒”(曾繪制多張作品),或許并非那座姚孟起題寫軒名的建筑,而是因為蘇軾的驚艷之問:“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這是一種發問,也是一種審視。蘇東坡的問號,是尋求超脫的人生空幻感;姚孟起的題名,是借典以抒情的風雅。但在今人看來,與誰同坐的追問,似乎恰恰是中西碰撞帶來的關乎自己與他人、過去與未來的困惑之問。巧合的是,這種中西碰撞的現實情境,倒也暗合了蘇軾發問時的慵懶之態—閑倚胡床。
責任編輯:張月霞
版面設計:湯煒
編輯:畫界 邢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