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書畫·現場>訊息訊息
從名畫中看全球化:17世紀的荷蘭小城與上海有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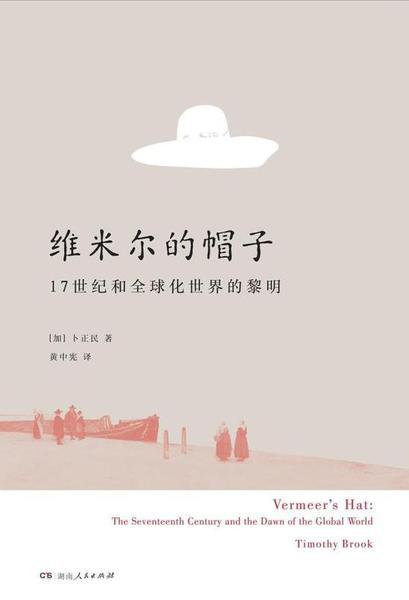
二十歲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買了輛腳踏車,往西南騎過荷蘭,展開從亞德里亞海濱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到蘇格蘭本尼維斯山(Ben Nevis)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騎在荷蘭鄉間,時近傍晚,天色開始變暗,從北海飄來的毛毛雨,把路面變得又濕又滑。一輛卡車擦身而過,把我逼到路邊,我一個不穩,連人帶車跌到爛泥里。我沒受傷,但渾身又濕又臟,擋泥板也給撞彎了,必須拉直。在外流浪,總會碰上壞天氣,我通常躲到橋下,但那時無橋可以棲身,于是我找上最近一戶人家,敲門請求避雨。奧茨胡恩太太早就從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車——我猜她有許多漫漫午后是在前窗邊度過的——因此,她開門露出一道縫,往外打量我時,我絲毫不覺驚訝。她遲疑了一會兒,然后甩開疑慮,把門大大打開,讓這個又濕又臟的狼狽加拿大青年進到屋里。
我想要的只是站著避一陣子雨,打理好精神就出發,但她不同意,反倒讓我洗了熱水澡,請我吃了一頓晚餐,留我住一晚,還硬塞給我幾樣她已故丈夫的東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明亮的陽光灑在廚房餐桌上,她請我吃了一頓我這輩子吃過最美味的早餐,然后赧然輕笑,說起她兒子若知道她留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家里過夜,而且還是個男人,會有多生氣。吃完早餐,她給我當地景點的明信片當紀念,建議我去其中幾個地方逛逛再上路。那個星期天早晨,陽光耀眼,我又不趕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議,出去隨便走走看看。我沒想到,就那隨意的一游,我與她所在的城鎮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給了我代爾夫特(Delft)。
“一座最賞心悅目的城鎮,每條街上都有好幾座橋和一條河”,以日記聞名于世的倫敦人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0年5月走訪代爾夫特時,如此描述這城鎮。他的描述與我所見絲毫無差,因為代爾夫特大體上仍維持17世紀時的模樣。那天早上,狀如15、16世紀西班牙大帆船的云朵,從西北邊十幾公里外的北海急涌而來,將斑駁云影灑在狹橋,以及大卵石鋪成的街道上,陽光映射在運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磚徹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意大利人以打入潮灘的木樁為基礎,建造出規模更為宏大的海上運河城市——威尼斯。荷蘭人所建的代爾夫特則與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代爾夫特以堤防擋住北海,開鑿有閘水道,排干沿海沼地。這段歷史就保留在代爾夫特這個字里頭,因為荷蘭語的delven,意為“挖鑿”。貫穿代爾夫特西城區的主運河,如今仍叫奧德代爾夫特(Oude Delft),意為“舊的有閘水道”。
從代爾夫特的兩座大型教堂,特別能看出17世紀的歷史面貌。位在大市場廣場(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興建時間比奧德代爾夫特運河邊的舊教堂晚了兩世紀,因此而得名。這兩座宏大建筑建造、裝飾之時(舊教堂是13世紀,新教堂15世紀)當然屬于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陽光從透明玻璃窗射進來,照亮教堂內部,抹掉了那段早期歷史,只呈現之后所發生的事情: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包括在1560年代拆掉教堂的彩繪玻璃)、將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會所。當時的荷蘭人為了擺脫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統治,多方抗爭,而禁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風就是其中之一。兩座教堂的地面大體是17世紀的古跡,因為上面布有銘文,用以標示17世紀代爾夫特有錢市民墳墓的所在。當時的人希望埋骨之處離圣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邊好。歷來有無數畫作描繪這兩座教堂的內部,其中有許多幅畫里可見一塊抬起的鋪砌石,偶爾甚至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著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戶人家埋葬地點的紀錄簿,但大部分墳墓沒有刻上墓志銘。只有負擔得起立碑費用的人,才會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誼。

在舊教堂里,我碰巧看到一塊刻有約翰內斯·維米爾1632-1675的石頭,每個字刻得工整而樸實。幾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欣賞過維米爾的畫作,想不到竟會無意中在這里碰上這位藝術家的最后遺物。我對代爾夫特或維米爾與代爾夫特的關系一無所知。但突然間,他就出現在我面前,等著我打量。
許多年后,我得知那塊石頭并非他死時就鋪在墓上。當時,維米爾還算不上是大人物,沒資格擁有刻了銘文的墓碑。他只是個畫家而已,某個還不錯的行業里的一名工匠。沒錯,維米爾是圣路加手工藝人工會的領導之一,而且在該鎮的民兵組織里位居高位——但他的鄰居里,還有約八十個人擁有同樣的高位。他死時一貧如洗,即使他死時有錢,那也不足以讓他有資格享有銘文墓碑的殊榮。一直要到19世紀,收藏家和博物館館長才把維米爾幽微縹緲、難以捉摸的畫作視為大師之作。如今所見的那塊石碑是到了20世紀才擺上,好讓許多知道他埋骨之處而特意前來憑吊的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處而無意間碰上——能一償所愿。但是那塊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實并非維米爾真正埋葬之處,因為1921年大火之后,教堂重建,所有鋪砌的石頭全被拆掉再重鋪。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遺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處而已。
維米爾在代爾夫特生活的痕跡,除了埋骨處之外,其余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場廣場附近他父親的客棧長大。長大后,大部分歲月在舊長堤上他岳母瑪麗亞·廷斯(Maria Thins)家度過。在岳母家一樓,圍繞他的子女愈來愈多;在二樓,他畫了大部分的畫作。最后,四十三歲時,債臺高筑、靈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逝去。那棟房子在19世紀被拆掉。與維米爾在代爾夫特生活有關的具體東西,無一留存。
欲一窺維米爾的世界,只有透過他的畫作,但是在代爾夫特,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畫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于波士頓的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但是在1990年失竊,至今下落不明),沒有一幅留在代爾夫特。那些畫作全在他死后賣掉,或運到別處拍賣,如今散落在從曼哈頓到柏林的十七座美術館里。離代爾夫特最近的三幅畫作,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這三幅畫離代爾夫特不遠——17世紀時搭內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個小時,如今搭火車只消十分鐘——但終究不在他畫那些畫的所在地。要看維米爾的畫,就要到代爾夫特以外的地方。在代爾夫特,就要斷了親眼目睹維米爾畫作的念頭。

維米爾畫作《代爾夫特景色》,1660-1661年作,現藏于荷蘭海牙莫瑞修斯博物館。
維米爾的繪畫生涯為何發跡自代爾夫特,而非別的地方,理由多不勝數,從當地的繪畫傳統到代爾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并不足以讓人斷定,維米爾若是住在荷蘭其他地方,就畫不出那么出色的畫作。環境很重要,但無法解釋所有的現象。同樣,我可以提出許多理由,說明17世紀人類生活的跨文化轉變這一全球史為何一定得從代爾夫特開始談起,但那些理由并無法讓人相信,代爾夫特是唯一一個應該作為起點的地方。事實上,那里所發生的事,除去可能改變了藝術史的進程之外,沒有一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而我也無意在這之外另發高論。我從代爾夫特開始談起,純粹是因為我碰巧在那里摔車,因為碰巧維米爾曾住在那里,因為我碰巧欣賞他的畫作。只要代爾夫特不擋住我們遠眺17世紀的世界,根據這些理由選擇該地作為審視17世紀之地,自然也無不可。
假設選擇別的地方作為講述這段故事的起點,結果又會如何呢?譬如說,選擇上海。因為第一次走訪代爾夫特又過了幾年之后我去了上海,而因為那趟上海之行,我成為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事實上,那同樣無悖于這本書的構想,因為歐洲和中國正是我在書中所描述互連磁場的兩極。若是選上海而棄代爾夫特,我所要講述的故事會有多大的改變?有可能改變不大。如果撇開顯而易見的差異,尋找那兩地的相似之處,上海其實和代爾夫特很相似。上海一如代爾夫特,建在原為海水所覆蓋的土地上,而且倚賴有閘水道排干上海所在的沼澤地(“上海”也可解為“居海上之洋”,但其實是“上海浦”的簡稱,意為“靠近河流源頭的有閘水道”)。上海同樣曾有城墻環繞(但只在16世紀中葉時修筑城墻,以防倭寇入侵)。上海本來有縱橫交錯的運河和橋梁,而且本來也有水路直通海上。新開墾的土地催生出發達的農業經濟,上海成為經濟的交易中心,并與周邊鄉間的商品生產的手工網絡緊密相連(當時是棉織品)。代爾夫特有城市中產階級,他們成為維米爾筆下的人物,雇請維米爾作畫,但上海沒有這樣的居民,文化、藝術的發展大概也大不如代爾夫特。但上海的富裕人家常贊助藝術,這和代爾夫特富商的行徑似乎頗為相似。更驚人的巧合乃是上海是董其昌的出生地。董其昌是當時最出色的畫家和書法家,改造了傳統繪畫手法,為近代中國藝術奠下基礎。稱董其昌是中國的維米爾,或稱維米爾是荷蘭的董其昌,都毫無道理,但兩人之間的相似處太過耐人尋味,無法略而不談。
講到代爾夫特與上海之間的差異,你或許會覺得兩地的相似只是表面。首先是規模上的差異:17世紀中葉時代爾夫特只有兩萬五千人,位居荷蘭第六大城市,至于上海,在1640年代饑荒、動亂之前,城居人口比代爾夫特多了一倍有余,鄉村人口則達五十萬。更重要的差異在于政治背景:代爾夫特是擺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后,新興共和國的重要基地,而上海則是明、清帝國牢牢掌控下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從規范其與外界互動的國家政策來看,代爾夫特、上海也必然涇渭分明。荷蘭政府積極建構遍及全球的貿易網,中國政府則是在與外國人接觸、通商方面忽禁忽開,政策搖擺不定(禁止通商的政策在當時中國內部引發激烈爭辯)。這些差異都不小,但我并不覺得重要,因為它們對我的目的影響不大。我寫此書的目的是去呈現一個更大的整體,一個人類正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建構聯系和交換網絡的世界,而上海、代爾夫特都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不管是從其中哪個開始談,故事在大體上都沒有什么兩樣。
選代爾夫特而棄上海,與前者還留存古代的氛圍有關。我在代爾夫特摔車,一腳跨進17世紀的氛圍,但若在上海摔車,就不會有這種際遇了。在豫園周邊的小街上,還殘存些許明朝風韻。豫園坐落在舊城的中心,乃是園主為了侍奉告老還鄉的父親,在16世紀末建成的。后來,以豫園為核心,興起一個小型的公共集會區,居民在此從事多種活動,包括藝術家到此掛出畫軸售賣。但在接下來幾百年里,這一帶蓋滿了房子,如今已少有遺跡可讓人一窺明朝時該地的風貌了。
但我以代爾夫特而非上海作為我故事的開端,還有一個特殊理由:維米爾留下了一批描繪代爾夫特風土人物的出色畫作,而董其昌則未留下這樣一批描繪上海的畫作。一等到經濟能力足以搬到縣城去住,董其昌就離開上海。維米爾則待在老家,畫下他周遭所見。瀏覽他的油畫,我們似乎進入栩栩如生的真人世界,在他們周圍環繞著充滿家庭氛圍的事物。他畫中的謎一樣的人物,帶著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的秘密,因為那是他們的世界,而不是我們的世界。但是他呈現那些人物的手法,似乎讓觀者覺得自己進入溫馨的私密空間。但那全是“似乎”。維米爾的繪畫手法太高明,高明到能欺騙觀者的眼睛,讓他們以為油畫只是個窗戶,透過那窗戶可以直接窺見他畫得仿若真實的地方。法國人稱這種繪畫上的欺騙手法為錯視畫法(trompe l‘oeil),意為“欺騙眼睛”。就維米爾來說,那些地方的確是真有其地,但可能和他筆下所呈現的差距頗大。維米爾畢竟不是攝影師,而是個錯覺畫家,運用錯覺藝術手法將觀者帶進他的世界,帶進17世紀中葉代爾夫特某個資產階級人家的世界。但即使真實的代爾夫特與他筆下有頗大差距,他的寫真畫作還是逼真到足以讓我們進入那個世界,思索我們所發現的東西。
在本書中,我們會根據維米爾的五幅畫作,還有與他同時代的代爾夫特同鄉亨德里克·范·德·布赫(Hendrik van der Burch)的一幅油畫、某個代爾夫特瓷盤上的裝飾畫,尋找代爾夫特人生活的蛛絲馬跡。我挑上這七幅畫,不只是因為畫中所呈現的內容,還因為畫中小地方隱藏了指向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搜尋那些小地方,我們會發現與畫中未充分表明的主題、未真正畫出的地方相關聯的潛在線索。那些小地方所透露的關聯,只是間接表明的關聯,但那些關聯確實存在。
如果那些關聯難以察覺,那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之前,還沒有那些。與其說17世紀是第一次接觸的時代,不如說是第二次接觸的時代來得貼切,因為那時候,初次相遇的地點正漸漸轉變成一再見面的場所。那時候,人們經常來往異地,并且攜帶行李同行——這意味著有事物落腳在制造地以外的地方,以新事物的姿態首次出現在那些新地方。不久之后,商業活動取而代之。移動于兩地之間,不再是那些偶然的旅人,而是為流通、販賣而生產的貨物,而荷蘭正是那些新貨物的集散地之一。在阿姆斯特丹——新貨物的匯集焦點——它們引來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注意。笛卡兒因為見解不見容于當道,不得不離開信仰天主教的法國,在尼德蘭度過漫長的流亡生涯。1631年,在流亡期間,他稱阿姆斯特丹是“貨物無奇不有”之地。他問道:“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種貨物和珍奇物品,這世上還有哪個地方比這座城市更能讓人如愿嗎?”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種貨物和珍奇物品”,當時的阿姆斯特丹的確是絕佳地方,至于原因呢,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自會明了。那些東西流往代爾夫特的數量較少,但還是有一些。有一些甚至落腳在維米爾所住的岳母瑪麗亞·廷斯家里,這從維米爾的妻子卡塔莉娜·博爾涅斯(Catharina Bolnes)在維米爾死后為申請破產所擬出的財產清單就可看出。維米爾還沒富裕到擁有許多好東西,但從他所得到的東西,可約略看出他在當時的地位。而要在哪里看到那些東西用于實際生活呢?就在他的畫里。
為了讓本書所要講述的故事不致枯燥,我要請大家仔細來看畫,說得更精確些,來看畫中的物品。這方法要有效,大家要暫時放掉某些既有的賞畫習慣,尤其是最常見的習慣——喜歡將畫作視為直接窺探另一時空的窗口。將維米爾的畫視為17世紀代爾夫特社會生活的傳形寫真,乃是迷人的錯覺。繪畫不是像照片那樣咔嚓一聲“拍下”,而是在小心而緩慢的過程中“造出”,而且它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客觀真實,不如說是想象中的特定情境。這個習慣心態會影響人如何看待畫中的事物。把畫看成窗口,就會把畫中的東西看成二維的細節,而且那些細節不是表明過去不同于我們今日的印象,就是表明過去和我們所知的過去一模一樣——在此,又把畫當成拍下的照片一般。看到一只17世紀的高腳杯,我們想:那是17世紀高腳杯的模樣,長得可真像/真不像(兩者擇一)今天的高腳杯。我們往往不會去思索:高腳杯在那里做什么用?誰制造的?來自哪里?為什么畫家將它,而不是別的東西——比如茶杯或玻璃罐——放入畫中?
本書鎖定七幅畫來探討,我希望大家定睛細看每一幅作品時,都只思索這些問題。大家還是能享有賞畫的樂趣,但我還希望大家深入畫中,仔細觀察畫中的細節,從中找出該畫繪于何時、何地的跡象。那些跡象大部分是在不知不覺中被畫進里頭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出那些跡象,以便利用畫作,不只了解畫的故事,還了解我們的故事。藝評家詹姆斯·埃爾金斯(James Elkins)說過,繪畫是必須破解的謎。我們覺得必須破解那道謎,以化解我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迷惑,減輕我們對于自己為何會置身如此世界的不確定感。我使用這七幅荷蘭畫作的用意,就在于此。
如果把那些畫中的東西視為供人開啟的門,而非窗口后的道具。那么我們會發覺自己置身在通道上,循著通道將對17世紀的面貌有所發現,而那些發現是畫作本身都未認知,畫家自己大概也不知曉的。在那些門后面,有意想不到的走廊和忽隱忽現的偏僻小徑,而我們叫人困惑的現在與一點也不簡單的過去,則透過那些走廊和小徑得以連接貫通,這連接的程度絕非我們能夠想象,而方式也會叫我們驚訝。檢視這些畫中的每樣東西,從中將看到17世紀代爾夫特的復雜過去,而如果有一個主題曲折貫穿那復雜的過去,那就是代爾夫特并不孤立。它存在于一個觸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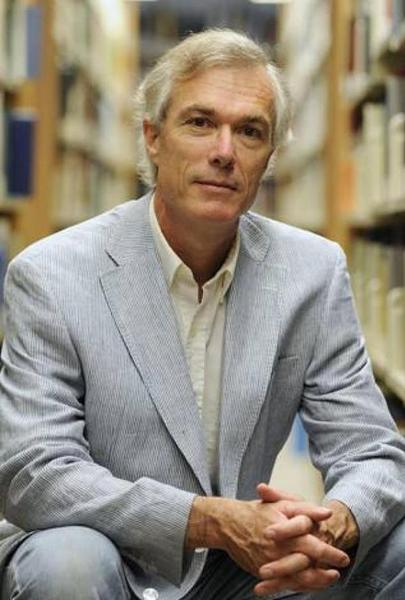
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2015—2016年度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會長。曾任多倫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學歷史學教授,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圣約翰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中國近代史、全球史,并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歷史》主編。2005年獲加拿大歷史協會頒發的歷史學獎項弗朗索瓦?澤維爾?加諾獎章,2006年獲頒古根海姆學術獎。代表著作有《縱樂的困惑》《維米爾的帽子》《為權力祈禱》《秩序的淪陷》《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等。
編輯:楊嵐
關鍵詞:米爾 上海 畫作 畫中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中國制造助力孟加拉國首條河底隧道項目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澳大利亞豬肉產業協會官員看好進博會機遇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官員說敘利亞約117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伊朗外長扎里夫宣布辭職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中國南極中山站迎來建站30周年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聯合國特使赴也門斡旋荷臺達撤軍事宜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以色列前能源部長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11年監禁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來首開夜場舉辦“燈會”
 法蒂瑪·馬合木提
法蒂瑪·馬合木提 王召明
王召明 王霞
王霞 辜勝阻
辜勝阻 聶震寧
聶震寧 錢學明
錢學明 孟青錄
孟青錄 郭晉云
郭晉云 許進
許進 李健
李健 覺醒法師
覺醒法師 呂鳳鼎
呂鳳鼎 賀鏗
賀鏗 金曼
金曼 黃維義
黃維義 關牧村
關牧村 陳華
陳華 陳景秋
陳景秋 秦百蘭
秦百蘭 張自立
張自立 郭松海
郭松海 李蘭
李蘭 房興耀
房興耀 池慧
池慧 柳斌杰
柳斌杰 曹義孫
曹義孫 毛新宇
毛新宇 詹國樞
詹國樞 朱永新
朱永新 張曉梅
張曉梅 焦加良
焦加良 張連起
張連起 龍墨
龍墨 王名
王名 何水法
何水法 李延生
李延生 鞏漢林
鞏漢林 李勝素
李勝素 施杰
施杰 王亞非
王亞非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姚愛興
姚愛興 賈寶蘭
賈寶蘭 謝衛
謝衛 湯素蘭
湯素蘭 黃信陽
黃信陽 張其成
張其成 潘魯生
潘魯生 馮丹藜
馮丹藜 艾克拜爾·米吉提
艾克拜爾·米吉提 袁熙坤
袁熙坤 毛新宇
毛新宇 學誠法師
學誠法師 宗立成
宗立成 梁鳳儀
梁鳳儀 施 杰
施 杰 張曉梅
張曉梅


